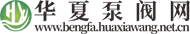第二天起床,竟是被鸡叫起的。早上观览了许多农业方面设备,比如说检测水分用的一个个土壤方格,其误差就只有0.01克。各式各样的传感器把数据送入中央计算机,再由中央计算机对数据进行分析和监测,如果有较大的变动就会发出警告。平时章老师也会在固定的时间检查数据。
但毕竟是个研学活动,学的内容是不少了,还整了不少活动,比如——抓鸡。因为张晓浮体格太差,昨天走那么远,直接把脚关节走伤了,走路慢吞吞的,只能让我我一个在上面到处追,但在机动性和身体灵活上我实在是差鸡太多。最后还是由步行机器人一枪带走的,之后便成了我们的午饭。
在说午饭前,不得不说农业活动,我想是一定会有的,种地向来是华夏名族离不开话题,但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大多连土地都没有踏上几回。
 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“想起以前帮家里人打油菜了。”
“你这样的还能干农活?”
“能但不多,当代的学习已经剥夺了我参与生产的大部分可能了。”
张晓浮从小是生活在农村的,但在农业上的知识我们两其实大差不差,毕竟他的父母大概率不是农民,可能爷爷都不会是,只是有个农村老家罢了。可我还是能感受到土地对他的吸引力,各种活动他都要去试试,也不管现在有没有这样的生产工序。章老师也是被他的积极弄得悲喜交加,我也只得在两人间多做点体力工作。
顺带一提,我自己也是喜欢这样的朴实的土地的。
吃食是可以自己带的,但怎么也得吃吃循环来的东西。来之前我还以为有什么虫子大餐,但实际的吃食是相当阳间的。土豆、米饭、茄子、蛋还有今天格外的鸡(早饭也能吃到猪肉的)。
“我还想年轻人都会喜欢些剧烈的活动呢。”
“章老师,现在年轻人体格怕是没有您一半的,精气神也是垂死的。”
“我看你们还是挺有上进心的,小伙子嘛。”
听到这样的回答,我和张晓浮都不由的乐了,异口同声的说:“可能吧。”
饭后我们聊了许久关于青年人的事情,大多都是我和张晓浮的抱怨,后来想起也蛮对不起章老师的,都快到了退休的年龄还要听我们叨念这些不大好的事情。
章老师给了我们很多自由的时间,但由于我和张晓浮都比较好奇科学家的工作,一直都像个跟屁虫一样跟在章老师身后,但不会问什么问题,只是安静的看看,有时问问春晓是怎样、怎么回事。
抱着这样的态度,我和张晓浮都记了十几页的笔记,特别在农业的部分——可以说是很丢人的——问了像怎么种地这样的问题。然后就是关于信息分析和AI方面的知识,由于AI可能关乎我们学业,张晓浮就借着机会给我简单科普了一些常识,比如限制性强人工智能能是没有主观能动性的,只是通过大量收集数据,做到在回答问题上甄别和使用相关要素罢了,因此和人类是有本质的区别的。
星火二号内是有大量自动化设备的,一些难以在市面上看到的自动化器械可以在这里大饱眼福,由于研学活动的缘故,有些样机下还写满的介绍。而随着笔记的增添,时间再一次到了晚上。通明的灯光染黄了窗旁的树叶,我们一起趴在木质地板上相互交换笔记看。
他的字和我差不多,都是那种直直的块块的,内容上和我大差不差,有的差别也是我要补上的。
“你说地下城,在目前环境下有什么作用啊?”张晓浮突然问我。
“你不是说第五次大冰期嘛,住到地下不就能抗寒冷了吗?我感觉。”
“我的想法是能保护未来大规模的电子信息,像EMP这种东西在信息化程度越高的地区产生的杀伤力就越大。”
“嗯,那还原生态就不是必要的吧?”
“你要想想人类的EMP主要能来自哪里。”
“哪里?”
“核弹啊!”他猛地碰了一下我的胳膊喊道。
“确实!我记得生物圈二号的目的也是这个!”回忆起自己所记笔记我,也莫名激动起来。
“那你知道俄罗斯的地铁吗?”
我关上笔记,回头看向他说:“不知道。”
果不其然他又要讲一堆杂七杂八的知识了……
苏联地铁从到三线工程,可我们俩连澡都还没洗,等这人回想起洗澡的事来都已经到十点了,而且就是走到了浴室他都还要讲讲古巴导弹危机。
“当年赫鲁晓夫和肯尼迪都是非常紧张的,毕竟全人类的的命运都压在那里了。后来依照这个事件里的不信任问题,有人写了一本科幻小说,并上升到宇宙的角度了呢。”在流水的哄声下,我尽力辨别他的字语。
“就是把冷战两国转换成人类与外星人吧?”
“是这样的,与外星人的第一次接触,一直是科幻小说母命题。过去那个年达到现在,悲观主义是占大头的。但我不这么觉得,可能外星人就长我们这样呢?可能人类的生物形态是生命的唯一解呢?这不是自大,而是大自然的选择,不是我们决定了生命的标准,而是生命的标准决定了我们。依靠自然科学的普世规律制成语言,是能达成交流的,更何况高等文明的生产力更高,存在的意识形态也可能比我们先进。啊,我不是觉得这两者就一定绑定啊,在我看来,乐观和悲观都是捕风捉影罢了,两者谁的概率高问题,我的想法还是两者概率都不高。”
我没有接话,而是等他还有什么可讲的……
张晓浮也没有说话,大概是没活了,一直到他停水的间隙,才继续说道:“你在干什么?”
“我翻到你说的那本科幻小说了。”我这么回答道,自他开始喋喋不休我就开始捣鼓春晓了,标注了不少他提到过的知识——都是得后面再系统性的学的。
“诶!”他大叫了一声,地面的哒哒声加剧了,估计是想赶紧出来罢,还好我不和这家伙睡同一张床。
今天在各个生态群落里没少跑,稍稍往那个方向想我就感觉身子痒起来了。一回来就该洗澡的,一不小心就被这家伙拖了这么久,还被抢了先洗澡的机会。自然,他一出门我就跑到浴室里去了,着急出来讲事情,结果又落空的感觉怕是不好受吧。
他倒是没打算让淋浴中我的听他在外头大喊大叫,我听到的大多是他通过春晓在翻些什么,时不时出现春晓的三两句回复,但依旧不见其说话。直到我出了浴室门,看到他已经上了床,面色很凝重,对着那台机器呢喃着什么。
我没有第一时间管他,而是上到自己那边,顺带关了灯。从被角的方向看去,绿色的微光下他的面庞显得十分呆滞。
“你原来看科幻吗?”这是事先准备的第一句话。
“嗯,偶然的。”我没有接话,让他继续说道,“我感觉我一切都是靠偶然拼凑起来的。”
“哦?”
“我曾经一切都是平平无奇,什么也没有,无知麻木都是能在过去的我身上看到的。直到后来,蛮可笑的,只是因为一部科幻电影就改变我的人生路线。”
“哦。”
“其实就是里面有些带着强烈工业器械的大机械,人对于极大的事物很麻木的,几万米和一个天文单位的视觉效果相比是一样的,除非,你在这样的大距离上拉上一根线。你的目光就顺着的线而去,不断攀升,直达可观测的宇宙的边缘。这样,那些与我们无关的东西似乎就变得生动起来。且,如果那根线是人造的,你能体会的东西就又上了一层。‘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’可现在我们可以说,不过是青天罢了。人类的力量随着镜头螺旋上升,那种深入人心的震撼,真的会让一个小男孩起鸡皮疙瘩。如果现在的我要用最精简的字来表达,那就是——人类。很抽象,但‘人类’便是我最深刻的感知。而且在这个时代,我们是能在现实中看到的,就像在昨天那座城市里。”
“我也有那种感觉,能感觉到人很渺小,人类却很宏大吧……”我回想起自己看到空天飞机时的感想。反而因为自己的想法的清晰,让我不太敢自认为彼此的想法一致了。
“所以最好笑的部分来了,我小学作文那里,关于梦想的文章写得是想做一名工人,想把那种宏大的浪漫带进生活带进现实,呼——”说着他大呼了一口气。
接下来的情况,我大概能猜到了。
他抬头看向漆黑的天花板继续说:“其实也没那么多事情,只是老师提了一嘴然后全班轰然大笑罢了。那节课下课后,我当了三天的工人笑话,至于为什么只有三天,那是因为我一直没什么存在的关系。生在农村甚至不知道‘遍身罗绮者,不是养蚕人’的意思,所以说之前很无知罢。之后的事情就很简单了,我去学哲学了,也会去看一些社会学相关的内容。随着年龄的增长,也越发反骨起来,开始讨厌社会风气社会主流,整天都在问:‘凭什么悲观主义就比乐观主义好?’‘凭什么成熟,现实就是各种喷血各种惨?’‘凭什么幼稚不能有幼稚的价值?’‘人性为什么一会是善的,一会恶的,不是圣母就是暴君,既然都是极端都是相反的,又为什么又说是灰色的,然后又疯追捧残暴的人性然后贬低善良?’随着这样的反骨,甚至开始对政治好奇起来……当然我一辈子都不会碰那种东西,但也越发反骨起来,讨厌那些动不动对社会和政府阴阳怪气的人,他们明明也没有做到系统的分析,为什么就可以那样的大义铭然?他们就不怕看的不够深不够仔细吗?”
他越发激动起来,声音也是越来越大的。
“当然说这些没什么屁用,还是多读点书吧。”说着他立马塞回了被窝里,再不说话了……
之后的两天活动都过的很快,我们彼此间都不怎么说话,那些问题在我这里也挺纠葛的,满脑子都是矛盾矛盾。可研学的整个过程总还是快乐的,很多问题问章老师是能得到答案的,年轻人与上一代先进份子的交流是极其舒畅的。
而对张晓浮来说就更为深刻吧,第二天的早上他那一迷离的样子,被章老师拉走足足谈了三个小时。回来的时候脸面都哭红了,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,但那种思想上的依靠感,对于他来说是极其珍重的吧。
而到这最后,我们在各个生态群落走了一圈,特别在雨林的石阶上又读了半小时的书才恋恋不舍的走开。我和他都特别喜欢那种静悄悄凉飕飕的感觉,思绪只有在这种地方才能解缓一些。
三天后再看入口的白色通道和白色路面,有一种突兀的陌生感。身后就是星火二号,虽然时间不长,家的气息却比任何地方都要重。
“章老师再见。”我回头说道,挤满思绪的张晓浮也跟着重复一遍。
章老师没有说话,只是点点头,微笑着。
其实也没那么远,有联系方式就是了。但,我想我是没有理由再打扰的,曾经在初中加过的好友总是这样,加上了但从未聊过天。
离开时我们拖了蛮长的时间,大晚上的还是和张晓浮在下层城市上了公交,车子很准时,甚至连司机都不用来,到了城外才会上手动驾驶。车上很空旷,只有几位年轻的打工人在酣睡。我和他坐到后排靠窗距离地面也比较高的地方,大概一分钟车子就动了,再然后就并入茫茫车流,开始高速行驶。密集的几辆大货车挡住了车窗视野,而在阴影下,我歪着脖子躺倒在座椅上,想着小睡一会。
闭上眼,感受着车子的加速度,耳边疾驰的声音在车厢内回荡,显得轻慢了许多。经过站台的加速减速能让我知道大概时间,也就两三站的时间,张晓浮拍醒了我,指着窗外已经空况的视野,高架桥上,可以看到远远铺开的上层城市。
“这叫什么?天街上的边市?”我迷迷糊糊说。
“是天上的街市啦!没有边的事。”张晓浮敲了我两下,我反敲了一下他,指了指酣睡的青年。
“所以呢你还记得原文么?”我打着哈气,懒懒的问。
“呃,春晓?”
“切。”我瞥了一声,把春晓的语音音量拉低一些。
远远的街边明了,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……
耳边的诗句流动,天上的飞机打着灯,远处城市酣睡在月下,近处的街灯烘着金黄色的路面。在这个时代,天上总会建起街市的。
“所以说,工人伟大吧?”
“嗯。”
远处的光点是那样连成一线的,城市的宏大确实如他所讲的一样显现了出来。但随着这黄色光点的脉络延去,不知为何,我的感受却是时间的流动,时间的重压。
“但是没有单纯的工人……”